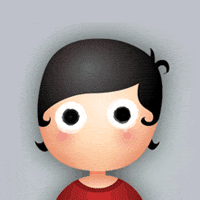和姥姥一起生活的日子
写在前面的话
非常感谢阿那亚社区的家史计划,使我们得以在这个过程中去回看我们这个平常百姓的家庭,回忆我们的长辈在曾经的岁月里所经历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也藉此重新认识我们自己。
李远江老师说:(我们)最需要铭记的不是往圣先贤,而是赋予你生命,塑造你人格的普通人。他们往往寂寂无名,是大历史的失踪者,无差别的统计数字。除了我们,没有人会留意他们的存在,也不会停下脚步倾听他们的故事。
在决定参加阿那亚家史计划之初,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要写一段姥姥的故事,写一段我和姥姥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我所记得的那些事。因为我是姥姥带大的孩子,姥姥是我至亲的亲人。
在这里,我不仅是想记录家族的历史,更多的是想以此方式,纪念我的亲人。
我的姥姥赵凤卿,生于一九零三年农历七月初七,属兔,是个普普通通的旧式老太太,没缠过足,但也不识字。姥姥这一辈子,历经了清末民初、战争、解放、土改、,虽没有波澜壮阔的人生履历,但却由自己点滴的生活感悟,形成了特有的人生哲学,并悄然地影响着我和我的家人。
姥姥自十八岁嫁人之后,便相夫教子,在大家庭里逆来顺受,就算在几次社会的变革之中家庭发生变故,就算是一次次家财尽失,姥姥也能总有一份平常而淡然的心去面对,不以物喜,也不以己悲。姥姥豁达的人生态度,多多少少的影响了我们家这两代人。的确,家史是量身定做的镜子,透过家史你会遇见历史深处的自己。
姥姥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几年了,因为城市的建设,姥姥的坟也找不到了,现在和以后,姥姥就住在我心里,住在全家人的心里,永远。
和姥姥一起生活的日子
姥姥走了······
那年冬末初春,姥姥走了,走的安详······
那天晚上,姥姥说:“想吃顿饺子。”我妈就开始和面,剁馅儿。馅儿是白菜馅儿,内时候北京的冬末,除了白菜还是白菜。一家人在北屋的炉子边上,围在桌边儿包饺子,姥姥坐在桌子边儿冲盹儿······饺子包完了,姥姥醒了。妈说:这就煮上吧?姥姥问:“煮什么呀?”妈说您不是想吃饺子吗?刚包得的!姥姥“哦”了一声儿,嘟囔了一句:“没说想吃饺子,不吃了。”饺子还是煮了,妈劝着姥姥还是吃了两个。吃完饺子姥姥就去睡了,这一睡,就睡到了永远······天没亮妈就喊我:“赶紧起来吧,你姥姥怕是不行了,你赶紧去给你姨儿送个信儿······”内会儿没电话,送个信儿就是得有人亲自去,我穿上棉袄出了门。我们家住鼓楼后头,我姨家住枣林前街,一北城一南城,我这一来一回,就是小半天儿,等我再回到家,家里的镜子都贴上了白纸,姥姥走了,我没见上最后一面。
打那儿以后,我的生活里就没有了姥姥。可我又觉得,姥姥一直在我身边,和姥姥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像一部旧电影,不断的在脑海中回放一个个片段,那一幅幅画面,也时常定格在心里。
老槐树下的童谣
从我记事起,就跟在姥姥身边。那时候我们全家都住在鼓楼后的院子里。
院子不大,南北对脸两排房,北屋两间半,南屋两间,贴着南屋的西山墙的半间,是个厕所,那时候自家院子里有个厕所也是个比较奢侈的事。院子的中间,有棵大槐树,树干很粗,粗到两个孩子是搂不过来的,树冠很大,大到几乎能把整个院子遮严。这棵大槐树,是我姥爷当年买下这所院子之后,从别处移来栽到院子里的,一棵槐树,另一棵是枣树。枣树长得慢,又是种在院子西墙的角落里,一直也没什么起色,一年也结不了半盆枣。倒是这棵槐树,长得遮阴蔽日。有了这棵树,一到夏天,小院里就洒满了花荫凉,姥姥带着我,摆个小桌子,上面铺张白纸,然后搬个小凳子坐在桌边上拉着我的手说歌谣。
姥姥不识字,会说的歌谣也不多,说来说去总是那几段,可我也还是总爱听那几段儿。“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姥姥姥姥抱我···”我就伸着手找姥姥抱了;“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哭咧咧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吗?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早上起来梳小辫儿!”“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子也要去,先搭棚,后挂彩,羊肉包子往上摆···”歌谣说完了,小桌子的白纸上面,会出现一粒粒的小东西,我和姥姥一人拿一根火柴棍,一点点粘着这些小粒粒往嘴里放,用舌头轻轻的舔那一丝丝的甜味,这些都是蜜蜂送给我们的美味。一天复一天,这些歌谣翻来覆去的说,我翻来覆去的听。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这样的日子,也许能一直下去,我会在这些歌谣中慢慢的长大。
但岁月,却并不能一直如歌,有时,也会骤起风波······
家被抄了,姥姥随着姥爷被轰回了乡下
,我们家鼓楼后的小院就没消停,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抄家。那时候我小,记忆是模糊的,我记得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家里人就没让我进院子,而是把我带到了对门儿戴姥姥家呆着。等到天快黑了,我才被领回家。进院子一看,家里东西都没了,院子的地也被翻了个乱七八糟,长大一点了才知道那就是抄家。据说是老家的人赶了马车来的,屋子里条案上的掸瓶、盆景砸的砸搬的搬,光是砸碎的瓷片都是成车拉走的,大都是清末民初的瓷器,有些还是我姥姥成亲时候娘家的陪嫁。抄家的原因很简单,我姥爷孙德芳土改的的时候定的成分的是地主。
上世纪八十年代人艺有一部话剧《狗儿爷涅槃》,当年看话剧的时候对剧中的老地主祁永年的印象颇为深刻,因为当时我就觉得这祁永年身上就有一些我姥爷的影子。就是守财的老财迷“一辈子没吃过一根儿直溜儿黄瓜,挨到过年才吃顿烙饼摊鸡蛋切细咸菜丝儿拌香油”的那种人。我姥爷常挂在嘴边儿的一句话:“愣买不值不买吃食”,多不值的东西,兹要买下了,就算是留了个物件儿,而吃,则是“穿肠过肚香嘴臭屁股”完全没有用!于是乎和怹的九叔一块在外面做
生意挣的钱,都拿回家来置了地、买了“不值”。地交给家里的亲戚种着,只求每年能管着我姥姥和孩子的吃喝就得,余下的都归亲戚哥儿弟兄们。然而“地”是我姥爷的名下产业,解放以后闹土改,就应了《狗儿爷》里的台词,工作组高声喝问:“谁是地主?”哥儿弟兄们齐指孙德芳:“他是地主!”所有亲情血脉统统皆无!从此孙德芳的名字前面有了前缀:“老地主”!不过要说我姥爷老地主孙德芳可是比老地主祁永年命大,至少在运动里没被打死,只不过损了钱财而已。
老家的“地”早在土改时候就归了大堆儿,,城里也不让姥爷姥姥这老两口住了,那时候凡是成分高的都得给轰回原籍。老两口离开了鼓楼后的小院,卷铺盖卷儿回了老家。
大槐树的花荫凉儿底下,小桌儿还在,却没有姥姥陪我拿火柴棍儿粘蜜蜂屎吃了,也没有姥姥跟我拍着手念“打花巴掌儿嘚”了。姥姥随着姥爷,回老家当地主去了。
随姥姥在乡下的日子
后来我也随姥姥去了老家。因为幼儿园闹传染病上板子关门了,爸妈整“运
动”、出差、做试验,反正没人看孩子,只好把我扔到乡下找我姥姥去了。
曾经的老地主孙德芳,轰回乡下之后简直就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赤贫,那些从前种着姥爷的地的哥儿弟兄们,那些亲戚里道儿的人们,没人接纳姥爷姥姥这老两口,倒是村里不沾亲不带故的富裕中农老徐家,收留了二老,腾出了一排北房中最西边的小耳房,这间耳房实实在在的一间屋子半间炕,几乎没有转身的地方,但好歹是间房,让二老容了身。
我回到村里,有了个新的名字:“老地主家的孩子”。我那几个二姥爷四姥爷们家里的闺女,虽是辈分比我高,按理我该管她们叫姨,但年岁却是相仿,我总想跟她们在一块儿玩,姥姥总是不愿意让我跟她们在一块儿玩儿,而且时不常的就会嘱咐我一句:“别让她们欺负你!”可我一个小孩儿,总是需要玩伴的呀,我们家住着老徐家的房子,老徐家最小的儿子,跟我差不多大,我闲的没事儿干,就只能跟他在一块玩,但男孩女孩总归是玩不到一块去,整天不是钻兔子窝就是站猪圈边上看猪拱食,要不就是跑到铁道边看火车,趴别人家窗户看屋里摆着的棺材。所以我还是变计八方儿的去找我那几个“姨”一块玩。我姥姥怕我亏着,总往我兜儿里放点钱,那个年月,我一个小孩,兜儿里总是能揣着两三块钱,也算是没有辱没了“老地主家的孩子”这个名号,我隔三差两的就花个一两毛钱在小铺儿买包糖子儿(就是没有独立包装纸的散装糖块儿,一毛钱能给小二十块儿),谁跟我好好玩,我就给谁糖吃(搁现在这种行为叫行贿)。
村里有个人叫窦傻子,当年是二十郎当岁儿,没个正经事儿,整天骑个破自行车在村子里瞎转悠,头一次在村里小铺儿门口看见我,就问:“你谁家孩子呀?”我说我孙德芳家的。窦傻子哦了一声:“敢情老地主家的呀!抓走吧!”。我当时一个几岁大点儿的孩子哪儿见过这阵势呀,心里除了害怕还是害怕,撒丫子就往家跑,窦傻子就在后面摇自行车铃,从打那次起,兹要我在村里听见自行车铃响,就撒丫子往家跑!后来这事儿就让我姥姥知道了,再往后更多的时候,就是我姥姥带着我出去玩儿。
姥姥领着我在一片开满了葱花的大葱地里抓老琉璃(就是蜻蜓),一个罗锅气喘的老太太,带着个黄皮蜡瘦的小丫头,在大葱地里扑腾,大葱地里的老琉璃特别的好抓,经常是一朵葱花上落着好几只老琉璃,一手伸过去能把几只都抓住,然后一个个夹在手指缝里,带回家,放进屋子里,姥姥说,这些老琉璃就帮咱们吃蚊子,这样咱们就不挨咬了。每次我看着老琉璃在那间转不过身的小屋里飞来飞去,心里想着不会挨咬的事儿,就能安心的睡觉了。
春天的时候,榆钱儿挂满了树,我姥姥会带着我,拿个布兜子从树枝子上撸榆钱儿,带回家洗干净,拌上棒子面上锅蒸,姥姥跟我说这叫榆钱儿扒拉儿。姥姥在灶边儿蒸扒拉儿,我就在院子门口玩儿,边玩儿边支愣着耳朵听着,一会儿我姥姥就得喊我:“快家来吃扒拉儿啦!”我跑回家,心满意足的吃着热腾腾带着清香味的榆钱儿扒拉儿,就像吃了满满的春天。
和姥姥一起在乡下的日子并不长,就让我爸妈给接回城里了。我读书写字学文化,每个礼拜天跟我妈一块儿坐着59路车去看我姥爷姥姥,每次回来的路上我都会看着车窗外渐渐后退的树林子自己偷偷的掉几滴眼泪,心疼姥爷姥姥孤零零的住在乡下······
直到姥爷去世,姥姥才被允许接回了城里,又回到了小院跟我们住在了一起。
姥姥做的好吃的
姥姥对吃颇为看重,嫁给我姥爷过了一辈子,两个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
观,比之我姥爷的“愣买不值不买吃食”,我姥姥倒是觉得“吃”比“不值”要实在的多,从小就听我姥姥说:“钱,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任谁到了儿也一样攥两把指甲走!吃好了比什么都管用,好歹落一肚子好下水!”
姥姥的这套观点与其说是对吃的看重,倒不如说是对钱财的轻视,如果不是这样,几次运动土改收了地、公私合营收了姥爷的买卖、,一个家财尽失的主妇,得熬淘成什么样啊!也正是姥姥对吃的最看重,让我们这些孩子得了不少倚,那个年月物质不能用不丰富来形容,几乎是要什么没什么,要是对吃再没点儿追求,那这人生简直就更加惨淡得没什么意义了。
我和我哥,几乎有着同样的记忆,就是姥姥给我们做的米饭。姥姥经常做捞饭,先用大锅煮米,七八成儿熟的时候用笊篱把米捞出来,放进铺好屉布的蒸锅继续蒸熟,剩下点儿米在汤里继续熬成粥。蒸熟的米饭盛在碗里,淋上点儿酱油,在点上几滴香油拌匀,那就是最好吃的米饭!至于姥姥为什么经常做捞饭,其实就是因为捞饭出数儿,那时候粮食都是定量供应,必须算计着吃。
每年端午节前包粽子,都是我们喜欢的事。每次包粽子之前,都是先把苇子叶和马莲泡好,江米和大枣也早早的泡好,然后搬着板凳大家围在桌边,姥姥一边包一边教我们包,姥姥包的粽子好看又好吃,包的时候先拿三片苇叶错开摞在一起理顺,两手向上分别拿住叶的两端,手向内一交错,让叶子正好形成漏斗状,江米带水放到里面,再放进两三颗泡好的大枣,交错的叶子两端向里折盖住漏斗,用虎口顺势一捏叶边就成了粽子形,中腰用马莲捆好,捆得越松蒸熟之后的粽子就越软,放进蒸锅蒸熟,那蒸锅里散出来的香味,留在了记忆里,也成了对姥姥的思念。
每逢家里人过生日,姥姥总是张罗着做顿打卤面。我记得最清楚的画面,是姥姥抻面时候的背影。一把面条在两只手中上下甩动,驼背的身体也会随之一颤一颤的,面条在这一颤一颤中越变越细······卤就更香了,黄花木耳鸡蛋肉,都是往常吃不着的,在姥姥精心的烹制之下,成了不同寻常的美味,于是每一次家人的生日,都过出了节日的欢喜。直到现在,我们家依然保留着过生日必吃打卤面的传统。
听妈妈讲姥爷和姥姥的故事
照片为我姥爷、姥姥和我妈(1940年)
每次说起姥姥,妈总是用这样的一句话开头:“唉,你姥姥这辈子,活的太
委屈!”说活的委屈,就是从打嫁给我姥爷开始的:“自打嫁到老孙家,就没过过舒心的日子!”这是紧跟着的第二句,我听的背下来,烂熟于心。
我姥姥在老孙家受的那些个委屈,我也的确听说过不少。
我姥姥的娘家,是做蜜供作坊的,虽说不是大富大贵,但在农村里日子还算过的不错。我姥姥生在这样的家庭,不是大家闺秀也算得上小家碧玉了。没上学没识字,不知书但却达理,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大声说过话。十八岁嫁给了我姥爷,进了大家庭。
我姥爷在怹的几个兄弟里,排行老大,我姥爷的爹在怹那一辈儿里也是行大,这么算下来我姥爷就算是长房长孙,在家里多少是有地位的,长大之后我姥爷跟着怹爹,出门在内外蒙古做生意,我姥姥嫁过来之后,大家庭里不知道是谁说的规矩,新过门儿的媳妇一年之内是不能同房的,我姥姥就没跟着我姥爷出去,留在了大家庭跟着婆婆过日子。再转过年,有了头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也就是我妈妈的大哥,我的大舅。我姥爷是个独子,这个新生的男孩就是孙家这一支的长孙,本该是备受呵护的,但没成想,就在这平民的大家庭里,居然也发生了宫斗的桥段。我姥爷的亲叔叔的一个孩子,也就是我妈的四爹,比我这位大舅早出生些日子,按说这叔侄俩能有什么宠可争呢,只因为四爹跟我这大舅同岁,当初我姥姥没孩子的时候,我妈的奶奶对小叔子的孩子挺疼的,但有了自己的亲孙子呢,我姥爷的叔叔就担心这嫂子不疼他们的孩子了,再说,这长房长孙将来是要继承家业的。嫉妒之情一直怀在心里,巴不得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
结果机会就来了。那一天我姥姥喂孩子吃奶,由于奶水足,孩子吃的时候就吃呛了,咳的翻了白眼,我姥姥年轻也没经历过事儿,急的就喊自己的婆婆,说您快来看看这孩子是怎么了,怎么翻白眼儿了?这话就让我姥爷的小叔叔两口子听见了,冲进屋里就把孩子从我姥姥怀里抢过来,说“这孩子眼瞅就不行啦,赶紧抱出去埋了吧!”就这么着,我姥姥的头一个孩子,活生生的就被埋了!耸人听闻的悲剧,我姥姥除了哭,什么也做不了,自己的男人不在家,一个女人能怎么样呢?
几年之后,姥姥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还是男孩。然而不幸的是,这个男孩也没能留住,四岁那年生病夭折了。姥姥连着失去了两个儿子,这也是在大家庭里抬不起头的,几个婶婆成天话里话外的嘲讽姥姥没儿子,下地干活的时候几个婶婆在一起互相搭手,姥姥只能一个人,种地背柴都是一个人干。姥姥年纪轻轻就得了哮喘,直到老年也没好。
在头一个孩子没了的十二年之后,我姥姥生了我妈,取名兆龄。
我妈一个女孩子,自然就不那么遭人嫉恨了,大家庭也分了家,我姥爷的一个九叔,也就是我妈的九爷,因为没儿没女,分到了我姥爷这支,这位九爷,一直跟我姥爷一起在外做生意,挣得的钱,回村买了地,还在包头市开了家烟酒石油店,取名“一大号”。后来九爷过世,财产都归到了我姥爷的名下。
于是我姥爷成了大家庭兄弟几个里的阔主儿。姥爷的一个三弟,是个匪,给姥爷扔了匿名信:“不给钱,就绑人!”为这,姥爷下决心把家眷们从那个家庭里接出来!1939年,姥爷花3000大洋买了鼓楼后的小院,谁也没告诉,悄悄的把九婶和姥姥一家人接了出来,跟谁也没说产业置在哪儿了。也是在那一年,我姥姥的哥哥,把他的小儿子过继给我我姥姥,我姥姥也总算是有了儿子。
一家人在城里过着自己的日子,1944年,姥姥又生了我姨。我姥爷在外做生意常年不回家,姥姥带着一家五口在家赊账过日子,实在接济不上的时候就把家里的东西当的当卖的卖,等年底我姥爷回来带回钱再还上。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1952年,土改开始了!
土改,姥爷姥姥被请回了乡下,不为别的,就为去定个成分,带了地主的帽子。我姥爷这辈子没过上地主作威作福的日子,却带了地主的帽子。地没就没了,反正从前也都是别人种着自己也没落什么好儿。
刚刚结束了土改,紧接着在1953年,从包头来了封信,让我姥爷回去,参加公私合营,我姥爷回了包头,土改没了地,公私合营没了买卖,我姥爷也由掌柜的,成了一名合营商店的店员,每个月按月拿工资。临回包头之前,我姥爷把我妈和我姨,还有我九老太太带回城里,我妈我姨一个上小学一个上中学,我姥姥带着我舅舅,又留在了乡下,我舅舅就在乡下上了学。
照片是我妈和我姨,在城里念书的时候拍的
姥姥带着我舅舅在乡下,乡下的亲戚也都知道了我舅舅是过继来的,于是依旧是各种嘲讽和欺辱,我那个五姥爷和六姥爷,曾经把我舅舅骗到庄稼地里打了个半死。这也是后来我随着姥姥在乡下住着的时候,姥姥一再叮嘱我别跟那些亲戚的孩子一块玩的原因了吧。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姥姥就这么委屈的过了一辈子,但也没听姥姥跟姥爷抱过屈,每天精心的照顾着家里的每一个人,只是有时候我妈会见到姥姥一个人偷偷的抹眼泪。
姥姥去世之后,我们与我姥爷家的那些亲戚,就不再有什么往来了,到现在,也没有往来,不想再有。不是所有血缘之亲都能维系亲情。
后记
我们和姥姥一起生活过的小院,现在已经夷为平地,老地主的最后一个房,也没有了。院子里我姥爷怹老人家亲手移栽的老槐树,也不见了。几年前我带着我的儿子,去看了还站立在一片废墟瓦砾之上的老槐树,我看着当年不到十岁的儿子张开双臂搂住大槐树粗壮的树干,仰头看着那如巨大的伞一样的树的枝叶,感觉就像我的姥爷姥姥在和怹们的重外孙深情的拥抱!那棵老槐树,曾经是一个家的根啊魂啊希望啊未来啊,真的,人要有根,有根,心就不惶惑了,生命就落地有声了,人的底气就足足的了。如今,树却没了。其实院子推倒也就那么大一块儿空地,如果不记录,除了我们家人,没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也没人知道曾经在这里的人有过怎样的故事。空间是这样,时间也是如此。人生匆匆几十载,除了心灵记忆,没有什么值得留存的东西。过去的总要过去,现在以至任何时候都保持平衡和希望就好!
2016-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