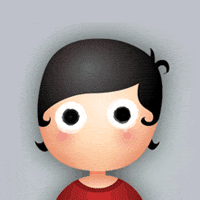潮汕坊间值得推荐的4大美味!
一碗好糜
说到潮汕饮食,必须从“糜”开始,糜就是潮州粥。
潮汕人对糜情有独钟。就像到了成都会满大街看见“冷啖杯、夜啤酒”的招牌,在潮汕,即便是夜里两三点钟,满大街的夜糜店仍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比北京的簋街不知热闹多少倍。
我在汕头最出名的夜糜店“富苑夜糜”吃宵夜,只见几张长桌依次排开,上面悬着明晃晃的白炽灯,几乎所有“打冷”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光是鱼饭就有红目连、伍笋、巴浪、那哥、金钱鱼、红鱼、姑鱼、佃鱼、小公鱼等十几种;还有一些传统潮式食物,如青蒜焖乌鱼、酸菜炣鳗鱼、炸排骨、香煎马鲛鱼等;、卤猪大肠、肥鹅肝、豆干等更是油光闪闪、堆积如山。这还不是全部,排挡上还摆放着小黄鱼、大斗鲳、活血鳗、虾蟹以及各种时令蔬菜,供客人随叫随炒。
面对这套“打冷豪华阵容”,有选择恐惧症的外地人往往无所适从,幸好同行的汕头朋友一语道破“天机”:不要被表象迷惑!这轰轰烈烈、气势如虹的排档再丰盛壮美,也不过是为了下得一碗白粥。有了这碗白粥垫底,潮汕人一天的生活才算熨帖妥当。的确,来“富苑夜糜”宵夜的本地人,全都一副平淡如水的架势,随意用手指点着,叫上几个小菜,就着一碗好糜,吃将起来。
潮州糜与广府粥不同,要用猛火,水一次加足,煮至米粒刚刚爆腰就算熟了。这时候整锅粥由余热糜化,米粒下沉,上面浮起一层如胶如脂的粥浆,就是潮州糜的特色。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讲过熬粥之道,说只有“水米交融,柔腻如一”才能称为粥。但这样半流质的白粥,要被潮州人笑话了。在他们看来,那就是难以充饥的“飞机糜”。
我们要了巴浪鱼饭、鲜炒薄壳和七八样杂咸,在一张木质圆桌前落座。潮州杂咸是一种佐餐小菜。对于潮汕人,假若喝白糜没有了杂咸,那真是要食不下咽了。
潮汕人习惯把小水产腌制的杂咸,称为“鲑”。比如,用虾苗腌制的称为“虾苗鲑”,用黄泥螺腌制的称为“钱螺鲑”,用小鱿鱼腌制的称为“厚尔鲑”。其他杂咸还包括用鱼露腌制的芥兰头、贡菜等。在过去,一小碟贡菜,几颗咸薄壳,也能下得几碗糜。
其实潮汕夜糜的特色是越传统越简单,以吃饱为目的。确实,这些盐渍的杂咸,恰恰说明潮汕料理并非阳春白雪,正因为从前贫穷,盐渍的东西才可下饭下粥。
此时,头顶一灯如豆,夜风清凉怡人。就着几样杂咸,喝上一碗潮州白糜,体验潮汕饮食的由奢入简,确是一件赏心乐事。
朋友说,来潮汕务必要这么个吃法。如果上来就是燕翅鲍鱼,就从根本上误解潮汕饮食的本质了。
传奇牛肉
潮汕菜是从何时开始风靡大江南北,甚至成为奢侈饮食的代名词的?
至少在公元819年,韩愈被贬至潮汕时,这里还是野象、鳄鱼横行的地方,编户数也只有万余户。在《初南食元十八协律》里,韩愈写到他在潮汕吃了鲎、蚝、蒲鱼、青蛙、章鱼、江瑶柱等数十种奇异的菜肴。与中原以“香”为特色的饮食习惯相比,潮汕的海鲜料理显然让河南人韩愈苦不堪言。
潮汕菜建立在以海洋文化为基础的“鲜”上,无论是腌、脍,还是白灼,为的都是尽量保持食材本身的味道,让食材充分发挥自身的鲜美。这种对“鲜”的执着,甚至体现在吃牛肉上。
汕头的牛肉火锅产生于上世纪40年代,传统是将沙茶酱直接加入锅中,像重庆火锅那样用浓汤作锅底。后来经过不断演变,现在锅底只剩下牛骨清汤和白萝卜,沙茶酱则被还原为酱碟佐料。这同样体现了对鲜的追求。
汕头最出名的牛肉火锅店无疑是八合里陋巷里的海记。有人甚至说,没吃过海记就算白来汕头了。我们去海记实地探访,海记的特色除了肉好,还在于斩肉的过程公开透明。试想傍晚时分,置身八合里小巷,空气中飘着鲜牛肉的甜香,几盏昏黄的灯火洒在长条形的肉案上。铁钩子挂着鲜红的牛腿、牛脊、牛尾,几个精壮的潮汕小伙一边谈笑风生,一边将手中的牛肉大卸八块,削成薄厚均匀的肉片。这是多么火热的生活场景,让人垂涎,也难怪海记能成为汕头牛肉火锅的典范了。据说,海记一年半之内就4次扩充营业面积,每天售卖的牛肉由开始的一头牛到10头牛。
其实,在汕头不愁吃不到好牛肉,位于东厦南路老飞厦市场的玉兰牛肉是海记之外的另一选择。这里环境干净一些,人也相对较少。我们在桌旁坐定,说吃火锅。转眼之间,汤锅、小料、杂咸、蔬菜就铺了一桌。巴掌大的菜单上写着“脖仁、匙柄、龙虾须、吊龙伴、胸口朥”等字眼,洋洋洒洒近二十种。这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名字,都是指牛肉的不同部位。
我们点了“脖仁”,这是指牛脖子中心活动最为频繁的那块肉,是牛肉中至为精华的部分,看上去像一块鲜红的花瓣上落满雪花。吃脖仁只需在汤锅中稍微一涮,即刻夹出,蘸一点沙茶酱或普宁豆瓣酱,鲜嫩的口感禁不住让人拍案叫绝。
接着是“吊龙伴”,特指牛脊肉的两个侧边;“龙虾须”则是牛骨盆夹缝中的那两条肉,形如龙虾须,因此得名;“正五花”长在牛后腿接近臀的位置,一头牛也只有两小块……我们一边大口啖肉,一边感叹,潮汕人竟然把牛肉吃到这么刁钻的份上。
曾经有人想把汕头牛肉火锅的经营模式复制到外地,但都不太成功。究其原因,汕头本土美食家张新民先生认为,汕头牛肉火锅之所以好吃,是因为它根植于整个牛肉产业链。从屠宰开始,大城市会对屠宰业进行管制,要求集中屠宰并对牛肉进行冷冻后才能出售。但汕头的牛屠是分散的,多数就在市区,屠宰分切后马上由专人用摩托飞车送往各个牛肉店,绝对没有经过冷冻。在新溪、外砂等郊区,还有前店后屠的格局,有时牛肉切上来,在盘里还会不停颤动。
最惊心动魄的一刻,发生在“胸口朥”端上来的瞬间。“胸口朥”特指牛胸口部分的那块牛油。被切成片状以后,白里泛黄,铺排成一盘,像泛着清甜气息的奶酪。这是汕头牛肉火锅最经典的一道菜,没有经过“胸口朥”的考验,就算不上食过汕头牛肉火锅。我夹起一块“胸口朥”,放进嘴里,味道甘美,肥而不腻,甚至连对肥油这一食材的偏见也一扫而光。
朋友把一块块涮好的胸口朥夹到我碗里,告诉我潮汕的食俗:一个男孩把一个女孩带到牛肉店吃火锅,点了胸口朥。如果女孩果敢地把它吃下,就代表内心深处已经认定这个男孩可托付终身了。
“我和老公当年就是吃了这顿火锅后决定结婚的,”朋友如是说。
牛杂老店
寻味潮汕,最大的感受是“高手在民间”。虽然我们也“吃访”了大林苑精细中菜馆、建业酒家等精品潮菜馆,但一圈吃下来,还是觉得真正的潮汕味道在街头巷尾的噪杂声里,在小本经营的淡然喜乐里,在对传统技艺的坚守发扬里。食物,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童年记忆。别看我的朋友现在挎着名牌包包,开着好车,当初还不是一放学就流着口水,凑到巷口粿条摊!
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潮汕料理俨然已经变成了奢侈宴请的代名词,可在潮汕地区,它还保持着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联的本色本味。所谓“礼失求诸野”,只有在市井深处,才能感受到食物自身焕发出的质朴尊严。
我们特意从汕头驱车来到潮州,只为去西湖公园边吃上一碗镇记牛杂。朋友说,这是她饕餮多年的记忆里,最完美的一碗牛杂。
镇记牛杂,祖传三代,已经开了几十年。如今依然是当年那个手工作坊的架势,连店址都没有变过。我们来时,正赶上雷雨,虽然是正午,可天黑得如同深夜。狂风席卷着街边的落叶,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我正抱怨来得不巧,朋友却说,要不是这样的天气,想吃上一碗牛杂粿条,要排上一小时的队呢!
饶是如此,不大的店里还是坐了不少客人,一个个都在闷头吃粿条,“吐噜吐噜”的吞食声,伴随着外面的狂风暴雨,有一种奇妙的感官效果,仿佛镇记是一个小小的诺亚方舟,载着吃货们最后的希望。
我们要了两份大碗的牛杂粿条,除了冒尖的牛杂、牛肉、牛肉丸,还配上了清口的豆芽,浇上了一大勺子金黄色的南姜。汤底的味道真是鲜美极了,牛杂又脆又嫩,豆芽烫得恰到好处,粿条清爽宜人,的确是我吃过最完美的牛杂。
虽说“觉得鸡蛋不错,又何必看下蛋的鸡”,我们还是禁不住走进厨房,与老板攀谈。老板是位散发着憨厚大哥气质的料理人,沉稳,寡言,却对自己的手艺充满自信,时不时会蹦出一段极具气场的发言。他偶尔起身到灶前烫牛杂,都是单手搞定,游刃有余。闲时便坐下喝功夫茶,用的是比茶壶还大的大茶缸和一个目测足有6L的超大烧水壶,十分豪放。
老板娘则健谈开朗,是典型的潮汕姿娘(姿娘,古时意为煮娘,即煮饭的娘子;现指妙龄女生,其特色为各种贤良,轻声细语,委婉温存),被老板称为“大姐”。大姐面色红润,皮肤极好。我们问其驻颜秘诀,她笑称应该得益于每天吃牛杂:“自家牛杂真材实料,汤底富含胶原蛋白!”
老板向我们证实,如非天气原因,店内客流量是极为惊人的。逢年过节更是大排长龙,一人购买几十碗的情况很常见,从北京、香港、东南亚等地专程赶来的食客屡见不鲜。
据老板介绍,镇记牛杂好吃,得益于真材实料。首先汤底是牛骨熬制,绝不含任何添加剂,保持原汁原味。再次食材新鲜,合作的牛肉店每隔两小时送一次货,保证客人吃到的都是最新鲜的食材(老板的祖父当年立下过规矩,未卖完的牛杂直接处理掉,不会留到第二天)。最后就是老板的手艺。牛杂的切工,烫牛杂的手法,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高深莫测的技术,是不可言传复制的。
老板用“打拳”给我们做比。切、烫牛杂是一门“功夫”,光有力气是不行的,技巧才是关键。必须抵达“手随心到”的境界,才能切出最恰当的牛杂,才能在最精确的零点几秒钟里,把口感最好的牛杂打捞出来。据说,曾有新加坡商人和老板谈过加盟,却被拒绝了。老板固执地认为,镇记牛杂的味道无法标准化,若非他本人,不可能做出那个味儿来。
如此闲聊之间,老板起身给自己烫了一碗牛杂粿条,感叹着,经营牛杂店数十年,每天都吃自家牛杂,不仅从不腻烦,还一次次被自家出品的美味震撼:“哇,怎么这么好吃!”
说这话时,老板一脸严肃,语气真诚,可爱至极。
深夜鱼生
寻找真正的潮汕味道,除了要有“老食煞”带路,也要有一点运气。比如,潮州的古法鱼生,在饭店里已经绝迹了,要想吃到,只有在夜半时分,去潮州老城的街头游逛,才有可能觅到。
潮汕话保留了不少古代汉语的词汇,如称“吃粥”为“食糜”,称“吃东西”为“食物件”,称“筷子”为“箸”,而潮州的古法鱼生保留的是古代“食脍”的习俗。要知道鱼生并不是日本独有,而是中国的鱼脍传到日本,被发扬光大的。
脍,指的是细切的生鱼片,要切得越薄越好,所以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苏东坡的诗里则说“运肘风生看斫脍,随刀雪落惊飞缕”,讲究的是细切的刀法。这与日本刺身的刀工风格也大相径庭。
晚上10点一过,我们像草原上饥饿的夜行动物,驾车出动了。潮州的夜晚比汕头清净,在迷离的夜色中,我们东张西望,寻找传说中的美味。
终于,在永护路和新桥路的交叉口,一家鱼生摊档进入视线。此时,老板正提着一尾活鱼准备制作。旁边早有几位骑着摩托的食客,停下车,静静等待着各自的宵夜。
潮汕虽然临海,可传统的古法鱼生,选的是沙池少泥味的草鱼。先于尾部的切口放血,然后打鳞开腹,用手撕去鱼皮,起出鱼背上两片没带骨刺的净肉。过程中如有血污,只能以净布抹干,绝不能水洗。之后,将整条净肉吊挂在铁钩子上,待吹失一定水分后,再切成薄如蝉翼的小片,摆放在竹篾中。这一食法,在清初广东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里就有详述,如今仍被那些遵从传统的鱼生摊档保留、恪守。
但见老板一边和周围的食客有说有笑,一边上下翻飞地细切着鱼肉。由于分量掌握得恰到好处,一块鱼肉正好铺满大半盘竹篾,而剩下的位置是留给配料的。这也正是潮州鱼生的特别之处。它并不像日本刺身一样,只配以酱油和芥末,而是对配料极为讲究。常见的配料就有菜脯丝、生萝卜丝、姜丝、葱丝、红辣椒丝、杨桃片、蒜片、花生末、南姜末、白糖、豆仁糖、米醋、生油、梅膏酱等。这五颜六色的配料与红肌白里的鱼肉搭配在同一盘竹篾里,在摊档一灯如豆下,显得既超现实,又妩媚动人。
老板的刀法娴熟,效率极高,前面的客人很快便提着各自的鱼生飘然而去。我们等待着自己的一份,心情如同等待过年的红包。老板说,其实食鱼生最好的季节是冬天。那时寒风乍起,被稍稍风干的鱼肉最为脆嫩鲜美。这时叫上三五好友,开一瓶好酒,吃完鱼生,还可再生个火炉,将鱼头煮成番葛糜——正应了旧潮歌里唱的:“半夜听见卖鱼生,想食鱼头熬番葛。”
这样的日子着实让人神往,我和朋友不由得立下誓约,冬日潮汕再聚。
来源:潮汕圈微信号,ACROSS穿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