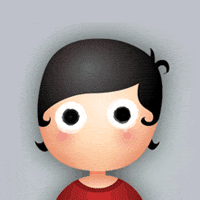十日谈 唐颖:配给年代过年忙
1936年霞飞路吕班路口,即今日淮海中路、重庆南路口
上海思南路
配给年代过年忙
唐颖
当年配给制,各样东西凭票证购买,各家人省吃俭用只等过年将圆台面弄得热热闹闹。家里那张可以折叠的圆台面从公用厨房的橱柜后面抽出来,过年期间,这张圆台面常被借用,像一个大轮子出现在弄堂里被滚动去不同人家。
现如今满世界的人在搭圆台面赴饭局,亲戚们却越来越疏于往来,好像当年的苦心经营让他们耗尽了心力,当然也因为前辈亲戚相继离世。
七十年代是个食物配给年代,单单一个粮食便有不同的配给标准,城里每户人家都有购粮证,记录了家中人口数,并按照性别年龄职业给予每个人不同的粮食定量标准。去米店买米买面或其他粮食类需出示购粮证,并严格限制大米购买数,每月每人大米购买数五斤左右。去点心店或饭店,或食品店买面包馒头这些谷物类点心都要付粮票。此外,食油食糖肉鱼蛋等要凭票,鸡鸭鹅等家禽以及海产到春节才供应,也会发票证,这些票证是根据户口本上人口分大户小户两个等级分发。四口和四口以下人家属于小户,五口和五口以上人家属于大户。我家五口人,是大户里的小户,加上母亲变戏法一般的操持,这年竟也过得有声有色。
父母祖籍都是宁波镇海,他们和他们的兄弟姐妹虽出生在上海,却有着浓厚的宁波人的生活习俗,不如说这习俗是互相影响得以保持。他们好面子规矩多,平时亲戚很少往来,因为不能空手上门,主人则要留客吃饭,留不住饭便拿个钢筋锅去点心店买点心招待,总之,亲戚间礼尚往来不能太随便。过个年就格外隆重,互相拜年连带赴家宴,假如说初一到初五只有五天假,那么午餐加晚餐共有十餐家宴,各家经过讨论协商排出互赴家宴的时间表,每家都要争取到一餐是请别家客,其余都是赴别家宴。由于还有老辈亲戚要拜年,所以每天要赶通告一般疾走三四家亲戚。
于是,每天两顿家宴常常重复地遇见亲戚们,有时中午刚在姑妈家吃饭,遇见了叔叔伯伯几家,晚上轮到我家请客,他们便转来我家,就像戏剧,场景换了角色未变。这一场接一场的请客,各家都在疲于奔命,却又不得不把“戏”演下去。
家宴繁多菜谱雷同,配给年代却要摆出八冷盘八热炒,因此,摆家宴的冷盆热炒必然是从嘴里省下来。匮乏年月备菜忙,母亲必须提前把肉和鱼腌制起来,她腌制的咸肉酱肉鳗鱼干黄鱼鲞比南货店卖出的腌制品咸度低更好吃。那年月妈妈最辛苦,她上班早出晚归,下班后忙不完的家务,却为过好每一个年竭尽全力。她不仅是为了满足做儿女的我们对节日的渴望,也是为父亲的心愿,他是这么童心,最欢喜看见孩子们的雀跃。在轮到我做主妇时,想想那些繁忙的年便心有余悸,好在过年最重要的年夜饭是在娘家吃。父亲去世后,这个家像失了魂,大年夜我和弟妹把母亲接出来,怀着难言的失落真让人怕过年。
想起备菜的日子,苦乐参半。年前一两个月最不好过,每月配给的肉和鱼不再上桌,却有一家店缓解我们的肉荒。
上海淮海路上的“茅万茂”
我们住的弄堂和另一条通向淮海路的弄堂连接,淮海路上有一家著名的酒栈“茅万茂”(沪语发音“冒饭某”,1980年更名为茅山酒家),就在这条弄堂旁边。茅氏酒栈门面和店堂一样宽,放有粗腿八仙桌,围着骨牌方凳,互不认识的酒客可在一张桌上喝酒,常常看到他们人手一只厚玻璃的啤酒mug杯。这里最时髦的是卖散装生啤,每天下午有一部像洒水车一样的啤酒运输车开来。那时没有酒吧,只有在茅万茅才能喝到新鲜生啤。也可外卖,啤酒从啤酒柜的龙头放出来。散装黄酒白酒是从桶里舀出经过漏斗到瓶里。酒桶放在店门处,于是这一处总是纷乱着顾客和过客。
重要的是,酒馆有个冷菜间,专卖下酒冷菜,有卤蛋豆腐干发芽豆,熟麻雀四分一只,肉汁百叶结一角十只,一角以上就可买到荤菜。父亲郁郁不得志,是茅万茂常客。他几乎每天傍晚去一趟酒馆,买一二两白酒有时黄酒,几角白切猪头肉或白切羊肉,熟肉不凭票呢!我们分享父亲的茅万茂下酒菜,而价廉物美的肉汁百叶结也很受母亲欢迎。
现在回想茅万茂的场景,对淮海路曾经有过这么一家只供酒不供饭的酒馆感到不可思议,尤其是在一个民间生活方式被消灭殆尽的年代,在社会面容如此严酷下,竟然有一家可以在此畅饮的酒馆,不能不说上海这个城市是有多么深的市民生活根基。不过,淮海路有过独一无二的店不止这一家,弟弟提醒我,我们曾经光顾并津津乐道的“牛奶棚”也非常具有场景感!因为她的后面真的是有个养牛场,在上海最“潮”的繁华街你能听到牛叫声,这里的牛奶必然最新鲜,这可是非常接地气的高大上,可当年牛奶是要通过医院证明你有慢性病才能订到。
七八十年代淮海路上的长春食品商店
上海西菜馆
七八十年代淮海中路上的庆丰熟食店
“牛奶棚”是俗称,它的正式名称是上海乳品二厂门市部,这家门市部其实是饮品店,内有一百多平米店堂,摆着简陋的铁凳铁桌,却因出售新鲜“掼奶油”而出名(“掼奶油”是用机器把新鲜奶油当场打松,四角一份装在高脚小碟),值得惊叹的是,“掼奶油”不仅是一种奶制品,它是那个时代被认为象征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意思的是,这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食品在上海总是一有空子就钻出来,包括“红房子”、“天鹅阁”、“德大”等西餐馆的西餐,老大昌的意大利冰糕,上海咖啡馆的热咖啡等等等等。
牛奶棚
掼奶油
无论如何,从嘴里省出来的家宴格外热闹,圆台面上喧嚣着“缺哪缺哪”的招呼声,不仅主人劝菜,客人也互相劝。“缺”是宁波人“吃”的发音,“哪”是语气词,连劝带求,十分诚恳。“下饭毋没饭缺饱!”宁波人把饭桌上的菜肴称为“下饭”,认为菜是用来下饭的?想来过去的宁波人但求吃饱不求美味。但是,明明满桌菜主人还在说“下饭”没有,在孩子们视角完全是睁眼瞎的胡言乱语。
每次亲戚们互相请客吃饭,整餐饭被“缺哪”“缺哪”的喧哗声填满,他们客来客去招呼,把餐桌时间打发了。我以后才会明白,亲戚们之间是不聊天的,没有什么话题值得一聊,隔墙有耳,他们害怕自己说错话,被紧邻的外人听见,也怕亲戚们把错话传出去。
“缺哪”了半天,餐后桌上的菜仍留存大半,有些甚至没有动过,砂锅里的整鸡,原封不动又端回去。春节每家每户有一只配給鸡。餐桌上八道热炒之后,必然要用砂锅端出整只鸡。
看起来这锅整鸡是摆样子,亲戚们彼此有默契,做客人的仿佛都有义务为东道主保留餐桌上唯一的整鸡,也许这整鸡在下一次请客时还能端出来。
说是请客,被请的客人不过是象征性地搛一两筷子菜而已,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在吃。而我们出去做客前,妈妈总是让我们先在家吃点心,于是坐在客人家的餐桌旁就没有了食欲,保持了斯文的吃相。
本埠有宁波人小气的说法,说他们一桌子菜是摆样子,不知从菜橱里端进端出几次。可仔细想想,并不单单是小气的问题。
食品开放后的这二十多年,为家宴精心准备的菜肴都能在餐馆吃到,虽然不那么地道,但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菜系纷纷进驻上海,你甚至都快抛弃在地家乡菜了。然而,有一样食物是我心心念念,却再也不可能吃到。无论多么有名的本帮或宁波餐馆,端出的宁波芝麻汤圆怎能跟当年我妈妈自己做的汤圆比?这是机绣和手绣的差异了。对我来说,曾经,过年最让我期待、排在第一的就是新年早晨的早点——汤圆。
妈妈的汤圆称得上极品,糯米粉又细又白,汤圆比二分分币稍稍大一些,小小的,但又不是太小,只只匀称,薄薄的皮白里透黑,咬一小口,芝麻馅就涌出来,我再也吃不到这么香肥细甜的芝麻馅。
这芝麻馅是花大功夫做出来的。首先选好芝麻,捡去碎石沙子在铁锅里用小火炒熟,然后用石臼舂碎,这件事由我和妹妹来做。舂碎的芝麻与绵白糖相混。当年绵白糖也限量供应,觉得不够时,便要用擀面杖把白砂糖捻碎。芝麻这一头弄好了,便是猪油的准备。关键是必须买到上好的肥白如雪花膏膘厚一寸以上的猪油,号称是大猪身的膘。为了这块猪油,妈妈要有几个清晨早起去肉摊排队,因为不是次次都有大猪膘。有了猪油,把芝麻白糖揉起来也并不简单。先要把猪膘上的筋和衣剥下来,这需要把一整块猪膘一点点扯下。从脂肪衣上剥下的膘才是真正柔软的油脂,这时才把芝麻白糖揉进猪油里。揉啊揉啊,直揉到猪油完全消融进芝麻白糖,成了一整块黑色的馅子,扯开任何一块见不到一点点白色的猪油,这馅子才上品,煮熟后咬开来流出的是纯黑的芝麻馅却又有猪油的肥香透明。这透明是看不见的,是在齿间感受的。
现在超市的冰冻汤圆,内里芝麻馅只是看起来像芝麻馅,进嘴后的混浊感像吃面粉,从此断了我吃汤圆的念头。
此外,汤圆糯软细滑的口感,也是精心打造的。我妈妈从不用干粉,只用水磨粉,也就是浸在水里的米粉。其工序是:先要把糯米浸几天,然后用石磨磨成粉。这活通常两个人干,也就是我和妹妹,一个掌磨子,一个加米,一般是磨两三圈,加小半调羹米,米不能加多,怕粉粒子粗,因此磨粉时妈妈会不时用手指捻一下磨出的粉,检查是否够细腻。连米带水磨成的水粉流进磨口下的缸里,先前的水粉,经过一个晚上,水和粉就分离,粉沉到水下,水是清澈的。为了保持水磨粉的新鲜,每隔两天就要换一次清水。需要用米粉时,先要用碗从缸里捞出粉到干净的米粉袋里,再把米粉袋吊起,直到袋里的水沥干,通常是三五个小时,这粉就可以搓圆子了。怎样在粉团里嵌入尽可能大的芝麻馅并保持汤圆外表的干净,则是手上的功夫,这个,我和我弟妹,我们三人都是一把好手。
年前我最喜欢的家务是磨水磨粉,通常石磨是放在厨房,厨房是两家公用在一楼,楼里人进进出出,后门就开着,隔壁人家也会进来看看。两家的煤气灶上都热气腾腾在煮年菜,厨房已预先洋溢节日气氛。
小年夜和妹妹一起坐在厨房磨粉,妈妈在灶上煮菜,或在砧板上刀斩煮熟的酱鸭或酱肉,她会捞起砧板上的碎肉放进我们嘴,那是我们在之后饭桌上感受不到那般浓烈的美味,所以妈妈总是说,砧板上的菜是最好吃的。后来回想,那是一段最有过年感觉的时光。
唐颖,上海出生,1982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6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来去何匆匆》,出版中篇小说集子《丽人公寓》、《无性伴侣》,《多情一代男》,《纯色的沙拉》。《瞬间之旅――我的东南亚》,《红颜――我的上海》,长篇单行本《美国来的妻子》,《无爱的上海》,《阿飞街女生》,《初夜》,《如花美眷》,非虚构长篇《加油小子――美国高中陪读笔记》,小说《红颜》曾被改编为电影《做头》,由关锦鹏监制,关之琳、霍建华主演。
收获微店
扫描二维码,进入购买页面
《收获》2017年第1期
2017年第1期《收获》目录
长篇小说
四世同堂·饥荒(老舍)
《四世同堂》英译全稿的发现和《饥荒》的回译(赵武平)
长篇连载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黄永玉)
中篇小说
红豆生南国(王安忆)
花匠与看门人(尹学芸)
短篇小说
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张楚)
逆位(斯继东)
十三姨(陈永和)
他们走向战场
我们歌颂我们之再生(严平)
三朵雨云
夜短梦长
老K,老A,和王(毛尖)
明亮的星
圣者(陈东东)
河汉遥寄
生命的感动(桂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