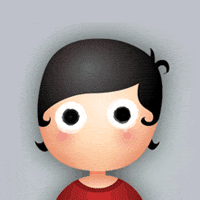虾虎鱼专栏丨一个朋克的十年
“毫无疑问,所有的人生都是一个垮掉的过程。”
(2006年5月 摄于迷笛音乐节 By 牛)
最近生了场病,神经衰弱、眼睛发炎与疑似肺炎早期等症状,伴随着我缠绵病榻的十多天。这也许是生活提出的正式警告:你得注意身体了!没想到,健康终于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使我清楚地感觉到----我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精力旺盛、可以没日没夜喝酒胡闹的年轻人了,而那一切,仅仅发生在十年前。
由于经常喝酒,我的记性不好,并且随着年龄增长,还有继续恶化的趋势。照这样发展下去,我毫不怀疑我将在耄耋来临之前就失去所有记忆。近年来开始整理从前写的东西,主要是修改一些小说,它们大多满腔热情但天真可笑,我想借此做个尝试,同时为无聊的生活找点乐子。毕竟,很多往事假如当时没有被记载下来,我是很难再度回想起来的。在其中一篇烂尾的公路小说里,一段十年前的旅程浮出水面,伴随着火车飞驰时车轮撞击铁轨那单调的声音,我看见二十出头的我坐在硬座车厢里,扎着头巾,身穿一件牛仔马甲,背后用丙烯颜料画着一个朋克头像。他没有面孔,在本该有五官的地方写着一句标语,“God Save The Queen”。
没错,这就是Sex Pistols的那首歌,因为当时的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朋克迷,热衷于把“革命”、“战斗”等字眼挂在嘴边,三句话不离“反抗精神”,视新金党为最大的敌人,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在各种摇滚BBS跟人吵架或拉帮结党,简单粗暴地认为热爱同类音乐的人都是“战友”,动辄就能跟他们聊上一整个通宵。我热爱摇滚乐,觉得身为一个朋克无比光荣,并经常被自己感动。那是二十一世纪初期,网络正在普及,我们得以接触到许多生活中无法触及的东西,而这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这儿说的“我们”,指的是一些当时因为摇滚乐结识,并最终跟我成为朋友的人,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卡生。去年底的一个晚上,我们通了几小时电话,她约我成立一个组织,开微信公众号也好,做别的也罢,总之继续用一些我们喜欢的方式做点有意思的事。这一点是很能打动我的,毕竟早在多年前,我们就一起做过BBS等许多事。当初她把我拉进了媒体行业,两年前我们相继转行,但对我们这些人而言,表达自己的想法与其说是习惯,反倒更近似一种本能。我们必需表达,没有条件,创造平台也要说话。
后来,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这个组织定名为“虾虎鱼”(这是另一个故事)。站在这个新的出发点,我首先想写写我们曾经的故事。关于这两个如今老大不小的女人,如何相识于不靠谱的摇滚青年时代,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了现在。这除了是对我个人生活的一种见证,更加是对我们友谊的纪念,因为今年是我跟卡生成为朋友的第十个年头。也许其中还有什么从前没能察觉的东西,甚至----我或许可以通过这些东西,再一次找回自己。
(2007年 摄于云南家中)
要知道,从前的我和现在的我,的确是两个人。如今人们喜欢在各种场合强调:我们生活在一个包容的时代。在我看来,这意味着许多从前“不正常”的事情,如今已沦为庸常。异端们不会再动不动就被挂上十字架进行审判,人们有充分的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事物,中庸的生活之道终于获得了胜利......这一切使我感到十分不习惯。这感觉就像身在某出荒诞戏剧中,人人带着假面和颜悦色,你总在想,背后会不会有诈、他们真实的模样到底是什么样儿?
换做从前,我们可不会这么想。一个来自云南边境小城的青年,只身一人坐上火车奔赴北方,跟许多素未谋面的网友见面,只为了大家一起去看一场音乐节。这样的事此后将再也不会发生---当时我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当我现在一点一滴回想起那些情景,心中涌动的还是那份感动,不改初衷。那时候从昆明到北京的特快列车只有两班,K61和K62,路程长达52个小时,硬座车票三百多块钱。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出这么远的门,一路上兴奋激动恨不得放声高歌。在那时的我看来,北京基本上就等于世界尽头。首都!大城市!摇滚乐!除了这些,脑子里想的只剩牛逼二字。
由于要先跟朋友们会合,我在石家庄下了火车。那会儿还没有土摇不土摇的说法,石家庄就是摇滚青年心中的圣地,因为这是《我爱摇滚乐》杂志的所在地。到那儿一看,说不颓是骗人的,天色灰黄,从周围的环境和街上的人身上,丝毫感觉不到任何摇滚氛围。那时我还不明白,其实内心有所向往的人,基本上都一厢情愿地生活在自己编织的幻梦中。接下来痛饮了两天,当地特产的嘉禾啤酒至今仍叫我记忆犹新,喝大后头简直痛得要裂开。第三天晚上,卡生从学校来了(当时她还在上大学),这是我跟她初次见面。第一印象如今已经模糊,大概记得是一个高瘦、头发和眉毛特别浓密的女孩,十足文艺青年打扮(大耳环、民族风头巾、对襟盘扣褂子等)。我们在KTV唱了黑豹、王菲和邓丽君的歌。喝大。后来又回旅馆继续喝到第二天早上。
我跟卡生在这之前就认识,通过共同的朋友介绍,说你俩都是云南人,都爱摇滚乐,又都写东西,可以交流交流。于是大家就朴实地加了QQ,互相发自己写的东西给对方看,在网上不眠不休地交流了好一阵子。卡生大学时代写过一个长篇小说《撕毁》,好像还得了奖,看完把我给震了,她在里边写了很多哲学命题,都是很究极那种,上帝和魔鬼讨论生存和死亡什么的。当时我认识的同龄人里没人写那样的东西,我想,操,这思想太牛逼了,长篇累牍地写了书评,俩人聊得没完没了。虽然我们对音乐的爱好并不一致,她喜欢哥特那个路子,但除了音乐之外,我们更多是在聊对写作和生活的看法,然后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并对我后来去北京从事媒体行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2006年那会儿,迷笛音乐节各方面已经趋向成熟,毕竟是第七届了,主题是“中国摇滚20年”,地点在北京海淀公园。关于演出的内容,我已经基本上想不起来了,反正后来成为标配的痛仰、扭机等乐队都有,还有一支我曾喜欢过但已解散的乐队摩天楼。这个事说起来立场十分矛盾,肯定是为了看音乐节才千里迢迢去的,但好像又不全是为了看演出。我们忙于在草地上喝酒瞎闹(并在喝大后闹了矛盾),到处跟不认识的人聊天拍照等等,并没有正经看演出。值得一提的是卡生当时自己印制了她的第一本诗集《路上的人都有把枪》,用行李箱拖了几十本去现场出售。在我此时残存的印象中,有不少画面都是我在草地上各处飞窜兜售诗集,价格好像是每本20块。
你可以发现我对我的记忆毫无信心,所有事都是“好像”发生过,“似乎”是那样。但要是让我谈谈当时的我们是什么样,还是有一些清晰的印象。首先大家都很瘦,都是特别纯粹的年青人模样;其次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甭管是谁坐下就喝,喝大了一言不合就动手;第三状态都特别飞,一方面怀有不切实际的、巨大的热情,另一方面又普遍充满愤怒、仇视生活。除了帮卡生卖诗集,我们还帮另一个朋友卖打口盘和LP,一张打口盘的价格在15到50不等,去七彩大世界按箱拿的话,合8块钱一张,严格说起来还是可以挣点儿钱。我也曾经动过在老家开个小店卖口盘的心思,后来当然没有实现,那时候每天都有无数个想法,但从来没有想过哪个真会实现。
我很早就想织脏辫,但没有任何途径,到石家庄后,我找了家理发店编了一头小辫子,扎上头巾,觉得自己特别有范儿。一种毫无来由的喜悦和亢奋笼罩着我,好像在那样的情境里,我终于成了我喜欢的那种人----自由、好看、独立、起范儿、与众不同,想喝酒就喝酒,喝多少都成,想pogo就pogo,不怕被撞倒,总而言之就是野。那份心气摒除了生活的一切限制,无视任何规矩,只为自己高兴,所谓无拘无束无非也就这样了,直到现在我依然能体会到那种自豪。
现在看来,2006年迷笛是我在音乐节的顶峰体验,可以在音乐节干的事几乎都干了,在迷笛学校露营过,住过西苑的地下室,甚至还去朋友在昌平的大学宿舍住了一晚上。所有的新鲜、刺激、未知、动荡都体验了,那么多年轻的面孔在一起碰撞,纯洁的革命友谊与激荡的思想,交流着所有天真的谵妄,捍卫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一场脆弱者、隐匿者与逃避者的狂欢,一切像短暂的白日梦般发狂。货真价实的乌托邦。后来大家一个接一个、毫无悬念地失去联络,曾经兴致勃勃彻夜聊过的话现在也一句都想不起来了。只有一首歌的旋律还会不时响起,那是我们在风扇村的时候听的《Hello Vietnam》。
2008年,我跟卡生第二次一起看音乐节,地点还是海淀公园,主办方摩登天空。我们依然没有认真看什么演出,还是随便往地上一坐,一杯接一杯喝啤酒。那一年我首次跟西安的朋友们见面,大家同样素未谋面。当我们喝大了在西苑某条漆黑的巷道中奔跑,大家一起高唱着“KKK took my baby away”,没有人在乎明天会发生什么。当我们坐在立交桥下垃圾场被丢弃的沙发上,触目所及是不远处立交桥上橘色的灯光。如果你问我生活是什么?我会说,生活是你用尽全力度过的每一个时刻。尽管所有好的坏的都会消逝,可是当你认真活的时候,你不会去想这些----它们如何消逝?它们是否还会再次降临在你的生命中?谁在乎呢。
(卡生&沈郁 2014年5月 摄于草莓音乐节)
2014年,我决定离开北京来上海。临走之前,约卡生看草莓音乐节。她本来不想去,觉得没意思,后来经不住我的劝说,还是一起去了。的确没什么意思,我们都不想看演出,在远离舞台的地方跟朋友一起喝酒。但对我而言这是某种仪式,离开北京毕竟是一个重大决定,我无从判断对错,只是知道需要去做。天擦黑的时候,突然刮起了大风,北京从来没有在5月刮过那么大的风,所有的垃圾和尘土飘扬在空中,状如一些人始终飘零、无可凭借的生活。当晚的演出半途结束,大风刮跑了舞台上的棚子,张曼玉刚唱几句就被迫下场,我们像逃难一样离开了通州运河公园。我的“前北京时代”最终迎来了一个兵荒马乱的、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结束。
有时候时间过得很慢,人老也长不大,只能在学校和课本中消磨时间。但有时候时间又的确在飞速消逝,不信你看,十年转眼就没了。2006年看迷笛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几年后我会去北京生活,那种唐吉柯德式的冒险,只是一个摇滚青年为了抵抗平庸的生活而做出的唯一可能的尝试,还有千千万万青年曾经或正在想尽自己可能的办法,逃离、反抗或在内心深处保持自我。在漫长的成人生活开始之前,许多人都会进行这样的努力,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我认为这一点是不会变的。就像我曾看到一个人写的他心中的北京:这座城市永远不会老,因为每天都有人奔向灿烂的青春。
“没路可走了”,“前面是什么”,“我有点儿害怕”----这些心情当时是没有的,就连想都想象不出来。我还特别狂妄地跟朋友说过,“30岁没死就等于白赚的”,不知道哪儿来的自信。我一直是怀疑生活那种人,但二十来岁的怀疑和三十多岁的怀疑也不是一种,活不到这天你完全不会知道。所以一直不敢掉以轻心,总觉得不知道哪儿就会有一坑,掉下去万劫不复那种感觉。但是又做不到小心翼翼活着,于是难免纠结。
摇滚乐和网络改变了我们这拨人的生活,前者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日渐远去的影子,我很久没看演出了,也不再会为此欣喜若狂或彻夜难眠,现在就连认真听音乐的时间都不多。生活让人疲惫,到了一个时候,你考虑最多的只是如何活下去、如何活得更好、怎么赚到更多的钱。你的精力和体力都大不如前。所以人们说,到什么山头只能唱什么歌。当我试图修改从前的小说,心中只有羞愧。那个不计一切也要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年青人不见了,她开始用一种别人的价值观来要求自己,并因改变的艰难而感到痛苦。她做不到什么都不要,可得到了也并不能使她快活。十年前她决心逃离一个牢笼,十年后却发现被关在另一个笼中。她还能挣脱一切继续前进吗?当回忆卷土重来,十年前的她和朋友们一起竖起了中指,“Why not?!”他们的脸上是目空一切的样子,他们说,“嘿!别装出那副熊样儿!”
后来大家亲切地把石家庄称为“庄里”,而我再没去过那儿。直到万青横空出世,厌倦地唱着,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那时候我特别喜欢格瓦拉说过的一句话,“我会一直站着直到你的枪响。”生活是最好的老师,终有一天你会明白,如果你把生活看作一场战争,那么这战争将永不结束。最终我们都长大了,在不同的地方过着各自的生活,从前觉得屈服是一种失败,但生活原本就没有对错可言。所以不要埋怨自己,也犯不着后悔,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要害怕质问自己:你选择的是你想要的吗?如果不是,你还敢不敢重新开始,再选一次?
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曾经身处同一阵线的、在同一个战壕里待过的战友们,现在都已失联了。只有我和卡生仍在并肩战斗,我们大概是有一些固执的,或许依然天真,无法忽视眼前的风车,也不愿意绕道而行。毕竟,这条路我们已经走了三十多年,尽管路程艰辛,好在风景还不赖,而且多的是脱离常规的事,足够刺激。这是一条值得继续走下去的路,正如我相信写作的永恒价值,并且我始终坚信,正是这份信念让我们走到了今天。命运早晚会让我们和一些人相遇,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其中某些人会让你知道,你可以让自己、以及不该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这故事离结束还早着呢。
(2015年 摄于上海红坊)
曾经我认为一个朋克的秉性是不会变的,现在我依然这么相信。“我将永远记得让我开始喜欢摇滚乐的那句话:去你妈逼的,全你妈滚蛋。这只是一种态度而已,它意味着不合作、不共赢、不低头哈腰,它使许多原始粗糙的东西焕发出强大的血性。我内心深处,将永远坚持朋克的虚无和反抗。”
“为了不从自我内部穿行,一直跋涉到世界尽头。走遍现实,方成为自我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