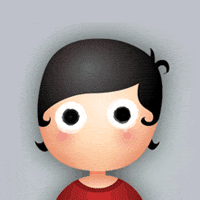【美文推送】殳俏:潮菜百态 一饭一传奇
礼失而求诸野,更何况潮菜本就是在潮汕之外始噪大名的菜系。海外潮人,永远比在地潮人更在意潮菜之“正统”。对细节的执著,是讲究,更是乡愁。
个人主义守护的田园风光
陪客人吃饭的时候,60多岁的钟成泉基本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动筷子。面对自己亲手研发出的满桌珍馐,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旁观者,顶多在身边坐了位女士的时候,他会冷不丁地挟起一份螺片,或是一片卤水,沉默地放进你的盘中,用低沉沙哑的嗓音说句:“食这个,这个好食。”
钟成泉是汕头“东海”餐厅的老板,而“东海”是屹立潮汕食界近30年不倒的金字招牌。同行都认为,在汕头这样一个遍地美食的城市里,虽有路边摊档街巷小店的繁荣,却也需要有高端料理的领军人物,而这样的人物,钟成泉算一个,能与其争锋的另几位,在现今的潮菜烹饪界,也都是颇具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
但显然,钟成泉不这么认为。“我入这行40年,从学徒做起,街头小食的粿也做过,牛肉丸也打过,进正规厨校,师傅最严格的传统潮菜训练我也受过,我学到的所有技术,是没有半点花架子的。‘东海’是我1984年开的,这里的每一道菜都经过我的脑子、我的手,我自认在汕头,一堆做菜厨子中间,我说自己算第二,就没有人敢在我面前称第一。”
看上去脾气温顺的当班经理,一边歪着头聆听老板的滔滔不绝,一边给我们分着“东海”引以为傲的白灼螺片。厚剪的响螺,据说一只一斤重的螺,其肥厚的螺肉经厨师用滚刀法片成相连的厚片,也就是舒展的一大片而已。片,是为了嫩而微微带点韧劲的嚼感,螺的细嫩,完全胜在流畅的刀功;而螺的鲜甜,则在于当堂白灼的技巧。以上汤灼螺,是为了最大化响螺的甘美,灼好后那一勺滚烫金黄的鸡油,则是为了封住响螺本身的鲜味和水分,让螺肉尝起来更加肥美多汁。
汕头“东海”老板钟成泉
每个人都举起筷子,想要多分几片淌着香浓鸡油的厚片响螺;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过来给我们泡工夫茶;有人互相频频举杯,听不清他们在说着什么喝酒的堂皇理由;几个吃到腾云驾雾的男客则在一边抽起了烟,谈论前一天晚上球赛的胜负,而钟成泉却有一种目中无人的霸气,可以声如洪钟地把他想要讲的,神闲气定地讲下去。
“现在外面所讲的潮菜,有很多夸大了潮汕人吃的东西,也有很多看低了潮汕人吃的东西。在我看来,潮菜无非是两个方面嘛,一种是海鲜,依我看,现在被外来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影响,越做越贵,但也没有做到多高明。另一种,在我看来是最亲切,也是最可惜的,就是潮菜里的田园风光。做田园风光的潮菜,所要用到的材料,有的很值钱,有的不值钱,但不管值不值钱,总之都在流失。”
滚热端上来的一个白瓷盅里,是钟成泉所迷恋的“田园风光”之一,一道簇拥着乳白细腻鸡茸的燕窝羹。这道鸡茸燕窝最大的亮点,是对鸡胸肉的处理。因为鸡胸肉不可随便在某块砧板上剁成鸡茸,而要取一块新鲜油亮的生猪皮垫在下面,方可开剁。此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挥刀剁向砧板时,砧板的微小木屑和经年累积在砧板上难以洗去的各种肉类脂肪微粒,影响鸡茸的油光水滑感以及鲜味的纯粹感。
生猪皮也不是可以随手拿来一垫了事的,要把猪皮内层的脂肪先刮干净。但要去除完全生的猪皮上的脂肪,其实非常困难,所以秘诀是汆水片刻,在猪皮的半生状态下捞起来,用刀把碍事的那一层刮干净,这才算妥。周围有人迅速赞这道传统潮菜恢复得好,并提出,在新加坡著名的潮菜餐厅“发记”,也有这道菜的出品。而钟成泉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前方,回应道:“新加坡的馆子做这道菜怎么样我不晓得,但我恢复这道菜只是因为自己喜欢,这种死脑筋的做菜法,我很喜欢。”
值此,竟又上了一大盆清汤牛肉丸。作为街头小吃,牛肉丸本不登大雅之堂,但出现在“东海”的筵席中,钟成泉自有他的道理。“客人常问我,这里什么最好吃,我回答他们,我觉得应该上桌的,推荐给他们的东西,都是最好吃的。当然,没有任何潮菜底子的客人,应该很难领会到这种‘好吃’的境界之高。”
邻座的汕头老饕迅速挟起一颗放进嘴里,边嚼边低声说:“嗯,这牛肉丸里加了鲽鱼干来丰富鲜味的层次,掺了一点点的肥肉丁以增加滑润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还有些许牛油的功劳,才能搞到这么香。”我开玩笑说:“那你去问问钟老板,看你猜得对不对,猜对了他可能会给你个奖品。”汕头老饕笑嘻嘻回答:“我才不敢,‘东海’一向不公布自家的菜谱,菜谱都在老板自己的脑子里,如果我猜到了他脑子里的东西,可能会获得追杀。”
传统潮菜鸡茸燕窝
作为一个强势的料理人,钟成泉的“老派”,其实代表着一种潮菜厨子的执著和顽固,这种执著,并非一味死守传统,而是忠于自我;这种顽固,也并非一成不变,只是作为一个厨师,坚持对自己味觉的无条件信赖。其实说到底,什么样的传统潮菜才能入得“东海”的法眼,上得“东海”的台面,完全取决于钟成泉一个人的信念。是以这里20多年如一日,没有菜单,因为钟成泉会决定,今天有什么好食材,可以让客人满意;这里也没有菜谱,因为所有的菜谱,都在钟成泉的脑子里,那些看似传承而来的老派潮菜,其实已经打上了深刻的钟氏烙印。
据说潮汕当地的厨师,多少都有点个人主义,他们拙于笑脸相迎,也不是那么善于听取旁人的意见。因为在这个地方,能对美食说出一番见解,且说得头头是道的专业和非专业人士都太多了,不被人影响,保护个人独树一帜的观念反而更加重要。所谓的“田园风光”,实际是一方不受人干扰的,宁静致远的小天地,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老厨师都可以躲进这片风光,琢磨着他的独门美食秘笈。
吃着煎粿条,我跟汕头老饕讨论着:“你觉得厨师需要霸气吗?一个真正的好厨师,到底是霸气地给予客人他认为最好的食物,还是体贴地根据客人的口味去着想?”
汕头老饕答:“当体贴成为一个厨师的潜意识时,他是可以很霸气的。”
潮汕之外的潮菜标杆
除了钻研做菜之外,蔡昊有时候也会在一些杂志上写威士忌如何搭配潮菜的专栏文章,篇篇都有种武侠小说的气质在里头,你来我往,高手过招,看完之后,胃口也有种虎虎生威的感受。
但说实话,什么都及不上老蔡亲手为你做顿饭。要注意,是亲手做饭。其实就算你千里迢迢赶去蔡昊的“大有轩”,也不一定有此口福。除非私交过硬,或是心血来潮,否则老蔡一定是躲人的。“大有轩的厨师肯定是做到极优水准的,不需要我亲自出马,而且,我是宅男嘛。”越是这么推诿,越是有识货的饕客死缠烂打,非要等到老蔡亲自下厨的那一顿。于是乎,吃着的人沾沾自喜,没吃着的人咬牙切齿“下次再来”。
所以,老蔡的出品到底有多神奇,比如他为某个扬言“这辈子都不吃胡萝卜”的朋友所悉心研制的胡萝卜,取的是胡萝卜的中段,先用清淡的高汤煮,使胡萝卜的青涩气味淡出;再放压力锅中与老鸡汤一起炖,使浓鲜味进入,这个过程的时间要短,因为时间长了,胡萝卜容易爆裂;然后把膨胀酥软的胡萝卜放入冰箱冷却几分钟,使激昂的纤维稍微收缩一下,同时也锁住了汤汁和水分;最后,再把胡萝卜煨一会儿,浇上熬好的鲍汁。
此时的胡萝卜,红艳如乌鱼子,酥柔如甜薯,味鲜如鲍鱼鸡,总之,无论你是看的,还是闻的,还是吃的,都很难一下子分辨出这仅是几段普普通通的胡萝卜。当你大呼美味的时候,老蔡会笑眯眯地说:“你不是说,这辈子都不吃胡萝卜的吗?”
“让我最着迷的,是食材的质感,以及这种质感在烹饪过程中的各种改变。”老蔡说,“其实我只是半路出家的厨子,只因为有段时间在美国南部开化工厂,地方太荒僻了,周围几乎没什么吃的,我就利用厂里的实验室做各种吃的,大多数时候,静静观察那些食材在温度下的改变是我的享受。时间一长,我意识到自己喜欢食物更甚于喜欢化学品,所以干脆改行开餐馆。”
上海“大有轩精细中菜”老板蔡昊
老蔡的“大有轩精细中菜”于2006年在上海开张。“精细中菜”这个名字不能迷惑那些懂行的食客,进来吃一顿,便赞不绝口:“实在是高手做出来的潮菜啊。”但老蔡还是会强调:“大有轩的出品,自然是潮菜的底子,但它的烹饪手法比较复杂;‘精细’说的是大有轩的做菜理念,是要往细节处考究,于细微处见真章,其实这也是传统潮菜很重要的烹饪理念。就算再草根的潮汕食物,都会有一个求精求细、注重细节的精神内核。
我不用‘潮菜’二字是因为不想太拘泥了,有时候大有轩也会使用非潮汕食材,比如大闸蟹什么的,但我一样会用潮菜的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去料理它。精细中菜是传统筵席潮菜的一个升级版,必须是很了解潮菜的老饕才能理解。所以,我这里常来常往的一些客人,都是‘懂的入’。”
去年最后一造的太湖大闸蟹,老蔡用饱和盐水、高度烈酒、大量蒜头和淡味酱油、芫荽等材料,将其腌制10到12小时之后捞起,用保鲜膜独立包紧,把冷库调到-15℃至-20℃,现在拿出来吃,口感是糯醉糯醉的,且滑嫩到每一口都可以把肉、蟹黄用舌头轻轻一吸即出来。
这样的做法是老蔡独创的,其中有潮汕腌蟹的灵魂,也有上海醉蟹的影子,但最重要的是“好吃”。唯有这最直接有力的“好吃”两字,可让人不讲出身,不争正统,也不计较到底怎样的做法才是“正确”。“其实所谓继承古法,也不是唯古法是好。继承,是要取传统中精华的部分,摒弃无用的繁文缛节。如果一味地为古法而古法,只重视过程的繁琐,忽略了最重要的‘好吃’的结果,那也是与潮菜的烹饪理念相悖的。”
老蔡当初选择在上海开大有轩,而非在家乡汕头,也是有如此的考虑在里头:“其实每次回到家乡汕头,看到老一辈做菜技艺出神入化的潮菜师傅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现在潮菜界所谓的中流砥柱们又墨守成规,止步不前,就会心生无限失望。
在中国,上海算是一个各种餐饮流派汇集一地的城市,每个厨师都会对自己擅长的菜式一丝不苟,但又不断与其他菜系碰撞、交流,每天都会有一些新东西吸收到脑子里,所以我觉得,也许上海就是大有轩的福地。”而这样的选择并没有辜负老蔡当初的期望,开业到现在,许多客人从香港、北京、台湾甚至海外搭飞机来到上海,只为吃大有轩的一顿饭。而汕头当地美食学会的几位资深潮菜研究者,也心悦诚服地向我推荐:“要吃最高境界的潮菜,其实你可以去上海的大有轩。”
“所以,我说了那么多,你作为客人,最喜欢大有轩的哪道菜?”老蔡问我。
我是俗人,若是带我亲朋好友来吃饭,一定必点大有轩的脆皮海参和脆皮大肠。这两个菜,其实有个共同的特点,体现大有轩对食材质感的终极追求,那就是“糯脆同体”的口感。脆皮海参,如果你想象一条传统的海参,一定是简单的黏而软,但如果你点大有轩的海参,你会了解到口感的层次分明是怎么回事。一开始舌头跟海参外表的接触,是浓汤芡汁带来的脆和香,然后以齿叩击,则一下子陷入了海参最令人期待的韧、糯、黏的质感,整个嘴巴的愉悦骤然沦陷在海参那带着海洋气息的脂膏之中。
对大肠来说,亦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口的感觉,必然是微微酥脆的表皮先给人惊艳的感觉,然后才把你带回你所期待的大肠头肥肉厚肥糯入味的嚼感。话说,所谓的食物“层次分明”有两个层面,一是嚼感的层次,二是口味的层次。这是在实验室把玩了多年食物的蔡昊所擅长的境界。潮菜于他,已是一种源于血脉的娴熟和自如。而老蔡的愿望,是钻研出更细致、更微妙的口感境界。
“如果你下次再来,我会亲手做浓汤龙虾给你吃。你知道这道龙虾要用心到什么程度?因为大多数人做龙虾,都是龙虾壳和龙虾肉一起去煮,煮的过程中时间一长,虾壳就钙化,会有让人不舒服的金属气息溢出。如果我给你做,就先用蒸的,保留龙虾肉的鲜甜,然后拆壳,将这壳单独去煨排骨,得到最鲜美的汤汁。
蒸好的龙虾肉则用手搓松它的纤维,千万不可用刀,用了刀,就得不到最松软弹牙的肉质。最后要把这分开料理的龙虾壳和龙虾肉再合并到一处,略炖煮一下,就得出这道菜的最佳状态。美味这件事情,在很多情况下,是别人对你的用心,分开料理,然后回归到一处,就这么简单,也是这么麻烦。”
“好,我下次再来,你得永远记得,你欠我一顿饭。”
通过食物维系的同乡之爱
“饭堂”主人吴浩然是个出生在香港的潮州人,家乡的美食和对童年生活的记忆养成了好吃的天性和对待食物的态度。在香港、日本、泰国生活多年后,他喜欢上了北京,觉得这里没有家乡的潮热而又有自由的氛围,连打高尔夫球都显得更畅快,那次他是在3月里降落北京,刚好去年春天的蓝天比较多。于是吴浩然决定留下来,更下决心开一家以前北京没有的住家味道的潮州菜馆。
到“饭堂”跟吴浩然吃晚饭,他拿出了珍藏的单枞茶,这是一个典型潮汕人对客人的欢迎方式,一边喝着工夫茶,一边聊一些我们共同的潮汕籍贯的朋友。其中一个大家都熟识的汕头女孩子,今晚即将迎接她的第二个儿子,正在医院待产。她的老公去陪床了,没办法照顾他们的大儿子,所以就干脆丢到“饭堂”。在北京这样的异地,无论发生什么事,来自潮汕的同乡朋友们都好似亲人,什么情况都可以帮忙解决。
“好吃的食物是潮汕人的骄傲,也是任何一个潮汕人之间可以沟通的语言。”吴浩然说,“这就是‘饭堂’的意义,它也许不是做菜做得最讲究的潮菜馆子,也不走那种公款消费会青睐的燕鲍翅路线,但在这里,你可以感到潮汕人的乡愁。我们经常会缺某种原材料,也经常会碰到非潮汕人的顾客对你提出‘今晚上就想吃个水煮鱼’这样的要求,但只要在这店里,某一桌聚集的都是潮汕人,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太温馨、太怀旧的气氛。一碗白糜和几个‘杂咸’,就足以让人觉得舒服了。潮汕人对自家食物的眷恋,外乡人基本都看不懂。在外地,吃不到自己家乡的东西,是莫大的折磨。‘饭堂’只能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去缓解一点这样的折磨。”
北京大多数的潮菜,走的都是奢侈吃喝的路线,金碧辉煌的酒楼里,清一色都是包间,每一扇门之后,鲍鱼龙虾都是“标配”。“但那样的客人,喝着大酒,已经完全不能感受到食材的朴素、鲜甜之感。”吴浩然说,“走进那样的潮菜馆子,我会觉得自己也接近半疯。潮菜对我们来说,是家,是童年,是母亲,是邻居家的婆婆,是小时候大家一起在海边玩,要我接受那样拜金主义的贵价潮菜,我真的会疯。”
所以,“饭堂”的样子很不一样。白色的清新色调,木质的桌椅摆设,点缀其间的绿植,粉红小碎花的沙发,搁板上摆放着四处搜罗来的仿古物件,做隔断的是排满杂志的大书架,看上去,你置身于一位高品位朋友的客厅。就连呈上来的菜单,都让人联想起童年时代的习字簿,干净又稚拙,完全像是个小朋友小心翼翼的作品。
“还是弄点东西给你吃吧。”吴浩然说,“你想吃什么?”
“那你弄点你小时候最喜欢的甜食给我试试吧。”
吴浩然起身去厨房,久久不出来,等回到桌边,则带着一道“白果芋泥”。潮汕人都知道,这是花工夫的一道甜点,要将普通的芋头做成芋泥,最浪费的就是时间。先挑选肉质干松的槟榔芋头,洗干净,去皮,切片,蒸熟,接着放在砧板上,将菜刀平放,揉压成芋茸。想做成无渣口感的芋泥,需要极细、极滑,所以得用菜刀碾压三遍以上,才能把小颗粒也都摆平。这时候,需一个洗得干净、没有异味的炒锅,先在锅里加热猪油,放几根青葱,炸香,但捞出不用。接着就是加入芋茸和白糖,使慢火,用锅铲不停地翻炒,直到芋茸、白糖、猪油完全融为一体。而在芋泥变得幼滑不黏手之前,还需加入煮熟的白果,来丰富这道甜品的口感。配着香味绵长的工夫茶,挖一勺芋泥,虽心知肥腻,却恋战甜美,不由得想要任性地全部吃完,这才是孩童时代对待食物的自然态度。
“童年,就是你故乡的食物,也是支持你在异乡打拼下去的力量。”
两种版本的乡愁
“最是乡愁是潮菜。”潮汕人对自家的食物魂牵梦萦,但是,于大部分外乡人来说,对粤菜和潮菜是区分不出所以然的。
有人听闻潮汕美食,便大呼“我最爱潮菜,比如烧鹅”,这便令人哑然失笑。粤食中的烧鹅,潮食中的卤鹅,也许南方人这种食鹅的习俗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从根本上来说,烧鹅和卤鹅并不是一回事。
而作为老潮汕的蔡澜,批评那些对潮菜一知半解的人更是厉害:“一般人上潮州餐馆,只懂叫卤水鹅片、川辣鸡、蚝烙、沙茶牛肉等普通菜式,其实潮州菜变化万千,如果娓娓道来,恐怕要写成一本电话簿。”
上世纪70年代,潮菜在香港忽然变得炙手可热,首先这种大规模的风行要归功于占香港1/5人口的潮汕人,他们在移民社会中,仍然一丝不苟地坚守着故乡的食俗;其次,则是几家高档潮州酒楼的成功,率先引领了这种潮汕饮食天下第一的风潮。这其中有暹罗燕窝潮州酒楼、环球潮州酒楼和金岛燕窝潮州酒楼,它们无不走精品潮菜的路线,推崇一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吃法,一方面让非潮汕人惊叹潮人之烹饪细工,另一方面则让老潮汕们感叹,这么动辄燕鲍翅的架势,实在不是潮菜本意。
花椒焗青蟹
有潮州籍老饕感慨地说,改革开放初期时,其他省份的人一听到你是广东人、潮汕人,便会觉得是大老板,顿顿吃龙虾、象鼻蚌。这样的错误概念大多来自香港人经营的走名贵路线的潮州餐厅,而住在香港的潮汕人若自己想去吃顿家乡味,则会选择大排档式的潮州菜肆,比如在九龙城城南道的“创发”。
“创发”门庭简朴,一走进去,却满眼是丰盛的食物:冻虾冻蟹、炸豆腐、煎马鲛鱼、炸小黄鱼,洋洋洒洒十几种。汤的选择也多,从胡椒猪肚到咸菜粉肠,从苦瓜排骨到莲藕猪脚。档上的游水海鲜和时令蔬菜可以任意捡择,要求店家按照自己喜好做成菜,或是干脆将美味大任交与厨子,这样的潮味老铺,搭配出来的味道一般都是耐人寻味的古早,奇怪不到哪里去。
这里的卤味,据说做得与潮汕当地比起来也难分伯仲。比如酱鸭,又比如搭配着鹅肠或鹅肝的卤鹅头。“创发”的很多食材,分明不是很昂贵的,却又能看得出,是花足了心思的。比如一碟小小的炸豆干,豆干是从普宁运来的,炸得酥脆嫩滑,蘸韭菜盐水吃,是千金难买的潮汕人的心头好。
蔡澜曾说,自己在香港的时候,也经常跑来“创发”,点生腌濑尿虾和冻小龙虾吃。而我在汕头的饕客朋友,听说我要写一家位于香港的潮菜时,望天思索良久,最后说:“还是创发吧。与其说一堆做得金碧辉煌的名贵酒楼,不如还是这家,算是在香港可以吃到乡土本味的真潮菜呢。”
比起传统乡土潮菜式微的香港,新加坡的潮菜,则是另一番风景。
同样可以援引蔡澜的见解:“潮菜,可以到南洋去找回原味。华侨们死脑筋,一成不变,传统潮菜倒是让他们留了下来,佼佼者有新加坡的‘发记’。他们的炊大鹰鲳,一刀片开,插上尖枝,像一张帆。再在鱼肚内塞两支瓷汤匙,这么一来,那么厚的鱼肉才炊得完美。”
“发记”位于新加坡厦门街的76号,主人李长豪是第二代传人,同时也是蔡澜的“发小”。那一道蔡澜赞不绝口的潮式古法炊鲳鱼,每条鲳鱼需片3刀,两面共6刀。一刀在鳍边,一刀在鱼背,一刀则剖尾。瓷汤匙塞入背和尾的缝中之后,还要塞进两粒浸得软熟的大个酸梅,鳍面的腹部,则要填入冬菇。鱼肚上也要铺冬菇,为的是怕蒸得过老,因为鱼肚部分最为薄。真正开蒸时,鱼上还要放红辣椒丝和茼蒿,铺上点肥猪肉,出锅之后,脂肪完全溶入鱼肉里,鲳鱼表面看上去闪闪发亮,鱼肉吃起来则肥美香甜。
作为固执地保留了最老派潮菜的餐馆,“发记”也承接最传统的“到会”业务。南洋人又叫“办桌”,意即把餐馆的菜搬到家里来,就连乳猪都可以到家里烤。蔡澜在文章中回忆,有一年他母亲办寿宴,李长豪就带着助手和两个女侍应,搬了家伙,浩浩荡荡来到蔡澜母亲家。乳猪两只,在店里已去了骨头,生完火,就支起铁架,在自家门后面的停车场上烤。
老式潮州的烤乳猪与粤式做法不同,广东人烤的是芝麻皮,要发细泡;潮式则是光皮,一个泡都不允许出。是以李长豪手执一柄尖细铁枝,看到有泡将要爆出,就迅速向肉中刺去,以保空气漏出,光皮回复平坦。
乳猪即将烤好时,猪头附近接触不到火位,有点不透,是以要再用一次铁叉,放在火炉架子的下面,用余温将猪头慢火熏熟到刚刚好。蔡澜感叹:“完全是一种艺术。”
礼失而求诸野,更何况潮菜本就是在潮汕之外始噪大名的菜系。海外潮人,永远比在地潮人更在意潮菜之“正统”。对细节的执著,是讲究,更是乡愁。
家宴大过天
潮汕人在自己家中开筵,那是了不得的事情。所谓的“做桌”,你可以请餐馆来家里大操大办,若自己有能力,亲自下厨更加难能可贵。在潮汕一带,能够“做桌”的人,是了不得的。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会成为众人争相邀请的焦点。还有所谓的“桌铺”,也就是做桌的班子,专门承接帮人上门办家宴,用蔡澜的话来说,他们是一群“流浪的厨子”,仿佛食界的马戏班一样,游走到哪里,即把做菜的手艺秀到哪里。
跟潮汕美食协会副会长张新民约好了,到汕头,一定要吃到他亲手做的家宴。待到约定的那天下午五六点钟,踏进张新民的家门,立即闻到一股悠扬的肉香味,张太太一边做十字绣一边告诉我:“他从清早忙到现在,弄卤大肠,弄鱼饭,整个人的精神处于极度亢奋,不做出最美味不罢休。”
家宴的菜单,则是用钢笔写在一张白纸上,是潮菜做桌最传统的“十二菜桌”,共计12道菜品,既丰盛又吉利的数字。分别是潮式卤大肠、花胶醉竹荪、小黄花鱼饭、鱿脯炒菌干、香煎凤尾鱼、咸柠檬炖鸭、花椒焗青蟹、豆酱炒麻叶、腌赤心虾姑、冬菜炒角瓜,加上两道甜点,光这文字便让人看得捶胸顿足,恨不能赶快开筵。
汕头美食家张新民
头一道是人见人爱的卤大肠。张新民捧着酱色腻人、油光锃亮的一大盆肥肠上桌,所有人立即都收了声,将中午饭抛到了九霄云外。“其实这卤大肠根本没有什么秘诀,就是要洗得干净点,干净点,再干净点。卤料要有八角、桂皮、小茴香、花椒、罗汉果、蒜头、南姜、芫荽。材料虽然多了点,但并不复杂,配好料之后装进纱布袋,用深锅放清水,加花雕酒、生抽、老抽,熬半小时就是卤水了。今天我买了5副大肠,洗得很干净,飞水之后就放到卤水里,煮到软糯,加清油和芫荽再煮片刻,就能捞起,切厚一点的片。如果你还想在大肠下面垫一些豆干片,那豆干就先得油炸,另外用卤汁浸到入味。吃的时候,不要忘记蘸点蒜泥醋,这样比较能中和肥肠的腻感,可以吃很多。”
小黄花鱼饭和花胶醉竹荪同时上桌,前者的鱼肉细嫩,质感微微弹牙,后者则清淡隽永,鲜得含蓄而不张扬。但这时,张太太开始点评:“鱼饭很好,花胶失水准。”张新民一个尴尬,便躲进了厨房,开始做青蟹。大家笑说:“味道都已经够让人惊艳了,看来张太太平时对先生要求很高。”张太太淡然地回答:“我这是为了激励他把菜做得更好,好的潮菜厨子不需要太多鼓励,有时候苛责也可以促人成长。”
吃完了鱿脯炒菌干、香煎凤尾鱼这两道味道相对来说香而重的菜,上来的是咸柠檬炖鸭,飘着柠檬清香的鲜鸭汤正好给大家荡涤一下嘴巴里的浓味,为下一道菜做准备。话说,这一道花椒焗青蟹,是张新民的独门自创菜,还未上桌,厨房里已是椒香四溢。“花椒看上去是四川菜里比较普遍的调味料,其实传统潮菜里也用到很多,比如干炸虾枣、花椒龙虾,而且越是古老的配方,花椒的使用量越是多,所以我受到启发,自创了这道花椒焗青蟹。也许吃着会觉得舌头发麻,但绝对是地道的潮汕味。”蟹黄涨得满满的青蟹要切块,先将油烧热,将葱段炒香后盛起,再将花椒热出味之后丢弃。然后才是将蟹块入锅,5分钟后蟹即被焗熟了,此时,是最关键的一步,张新民正在厨房里耐心地将花椒味的蟹汁不断地浇淋在蟹肉块上,直至全然入味,这才要把刚才热好的葱段倒回锅里,翻匀,然后就可以装盘上桌了。
青蟹肉厚,大口肥实的蟹肉被渲染得花椒香十足,微麻则更多地激发出蟹肉在嘴里的回甜,吃起来从脑到胃只变成一条直线,只愿无意识地吃个不停。硬实的蟹黄则是另一番滋味,浓厚的油脂遇到让人沁汗的花椒,产生出更让人无法抵抗的香甜。张新民擦擦额头上的油汗,微笑着说:“别着急,其实这还不是最精彩的。”
一道普宁豆酱炒黄麻叶,这才带出了新兴奋点。一盆生腌的赤心虾姑被端上来,青灰色的壳,你能看见那晶莹剔透的肉。所谓的“赤心”,即是虾姑含有丰富胶质的膏黄,金黄璀璨,几近赤红。“这种东西,我们潮汕人叫做‘毒药’。”张新民说,“因为会越吃越鲜,越吃越甜,越吃越想吃,是以就上了瘾,晚上做梦都还是各种生腌货。但最近几年,我们一般都在家自己做,自己吃,因为自家挑选的,一定是肉最饱足的,也一定是即买即吃最新鲜的,并且会洗得很干净,腌得很精心。所谓餐馆里的独门腌料,其实十有八九是噱头,吃虾姑只有两个标准,一是鲜甜弹牙,易于入口,二是总得有好酒搭配着。”
家宴的尾声,由一锅好糜画上圆满句号。煮潮州白糜,米粒刚爆腰,就要熄火,锅中余温会将糜继续熟化,最后糜粒下沉,最上方则积聚出一层洁白如凝脂的粥浆。盛糜时,必要既盛进糜粒,也要舀一些粥浆。说来奇怪,明明吃了那么多好东西,却仍对白糜心存向往,就着张新民拿出来的南姜腌的菜脯,一碗白糜徐徐落肚,只觉妥帖非常。淡定的张太太此时又发话:“我建议你们给今天的这顿家宴打80分,这样,张新民才会有动力,下一次再请你们来吃100分的饭。”
作者:殳俏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