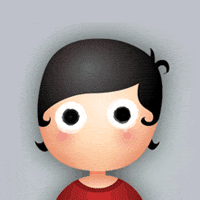如果不相信,头伸出老虎窗,啊夜,层层叠叠屋顶,“本滩”的哭腔,霓虹养眼,骨碌碌转光珠,软红十丈,万花如海。六十年代广播,是纶音玉诏,奉命维谨,澹雅胜繁华,之后再现“市光”的上海夜,风里一丝丝苏州河潮气,咸菜大汤黄鱼味道,氤氲四缭,听到音乐里反复一句女声,和你一起去巴黎呀和你一起去巴黎呀去巴黎呀。对面有了新房客了,窗口挂起的小衣裳,眼生的,黑瓦片上面,几支白翅膀飘动。
——金宇澄《繁花》
灯红酒绿,车水马龙,活色生香。老上海不是一张平面的年历片,而是一捧立体的绚烂的繁花。
回忆从五六十年代开始,有三个小囡从是赤膊兄弟。住在皋兰路洋房里、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囡,带着隔壁邻居家的妹妹看风景,两个人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眼里是半个卢湾区,前面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西面后方,,三十年代俄侨建立,据说是纪念苏维埃处决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东南风一劲,听见黄浦江船鸣,圆号宽广的嗡嗡声,抚慰少年人胸怀。
层层叠叠的复杂天际线下,上海的市井一向是五味杂陈的。住在大自鸣钟的阔太太叫邻居家工人阶级家的小囡,帮她第二一早排队去领红房子的就餐券,“明早六点半,帮我乘24路,到断命的红房子跑一趟,阿好。”旁边剃头的江北师傅讲,“讲什呢讲,做人,就要活络。”空军干部家的小囡,响应号召在弄堂里上的民办小学,说是小学,实际就是少奶奶、小姆妈让出私房当学堂。有一位张老师,一直是花旗袍打扮,前襟掖一条花色手绢,浑身香,这是瑞金路女房东,让出自家客堂间上课,天井内外,有人生煤炉,蒲扇啪嗒啪嗒,楼板滴水,有三个座位,允许撑伞,像张乐平的三毛读书图。通常上到第三节课,灶间飘来饭菜的油镬气,张老师放了粉笔,扭出课堂,跟隔壁的娘姨聊天,经常拈一块油煎带鱼,或是重油五香素鸡,转进来,边吃边教。无论什么时候,在浓得化不开的烟火气里,上海人总带着自己的名堂经过日子,特立独行,却鲜活无比。
即使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生活再拮据的时候,上海人在几平方米的房间里硬是要挤出一只角,安放一只玻璃橱,里面陈列着咖啡具、拉丝茶杯、长毛绒玩具、洋娃娃、唐三彩马、无锡大阿福以及空的茅台酒瓶……这叫“螺蛳壳里做道场”,左手怀抱浪漫主义情怀、右手紧抓现实主义态度,开出一朵独属上海的花。
改革了,开放了,资产阶级家的小囡开始做外贸生意。空军干部家的小囡念了大学读法律,跟女同学谈朋友。八十年代谈朋友,一般是看电影,逛公园,荡马路。美琪,平安电影院,设有情侣咖啡馆,伸手不见五指,一排排卡座,等于半夜三更长江轮船统舱,到处是男女昏沉发梦之音。后来两个人关系靠定了,男生经常去女生家里。女生住在新闸路的新式弄堂,弄堂曾经住过电影皇后阮玲玉,上三楼,每层三户,每家一块门帘。还好是新式弄堂,比较安静,上海称“钢窗蜡地”。如果是老式石库门前厢房,弹簧地板,一步三摇,板壁上方,有漏空隔栅,邻居骂小囡,唱绍兴戏,处于这种环境,男女朋友除非两人关灭电灯,一声不响,用太极静功,否则什么都干不了。
故事的最后,工人阶级的小囡一辈子游戏人间,在养老院里落魄而逝。空军干部的小囡和资产阶级的小囡依照他的遗言,帮他照顾借住在他房子里的一对法国青年。法国人雄心万丈地准备写一个上海剧本,但外人眼里的流行的上海传奇,终究只是一些烂俗的套路。真正大上海的风情,在大马路小弄堂里弯弯绕绕,闭上眼睛体会得到,睁开眼睛讲不出来。
“六十年代的少年旧梦,辐射广泛,处处人间烟火的斑斓记忆,九十年代的声色犬马,是一场接一场的流水席……小心翼翼的嘲讽,咄咄逼人的漫画,暗藏上海的时尚与流行;昨日的遗漏,或是明天的启示……即使繁花零落,死神到来,一曲终了,人犹未散。”
——金宇澄《繁花》
想要闭上眼睛体会上海独特的传奇与风情,想要聆听繁花里永不停歇的歌唱,7月11日,“上海医药”荣誉呈现2018上海夏季音乐节《繁花:电子乐与四重奏》,将用声音再现金宇澄笔下软红十丈,万花如海的老上海风情。
注:音乐会除了繁花的舞台剧配乐,还有B6其他的原创音乐。
戳“阅读原文”,推开老虎窗,回味大上海。